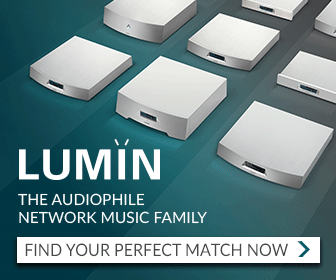跟往年比較,鮮浪潮的名字愈常出現在各大媒體的報道,屢屢傳出參賽作品不獲電影、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發出「核准證明書」(准映證)、取消放映的消息,引起大眾熱議香港的創作自由是否受損。來到本年第十七屆,最初因為邀請了男團 Mirror 的成員邱傲然(Tiger)執導開幕短片《是日精選》,成功吸引影迷以外的觀眾注意,並乘勢加場,為其他參賽作品帶來更多接觸大眾的機會;後來卻再度因為電檢問題,三部作品包括開幕短片《My Pen is Blue,》、競賽作品《未能接通》和《爺爺來訪的夜》被要求刪改內容,最後以黑畫面和靜音代替無法送檢的聲畫。就這樣,鮮浪潮再次因內容審查成為大眾焦點。 由杜琪峯發起的鮮浪潮國際短片節,一直為有志投身電影業界的人打開一道門。不論經驗多寡,只要參賽者遞交包含故事大綱及處理手法的拍攝計劃,讓評審團甄選,入圍者便會獲得 10 萬製作費。換句話說,創作人是向鮮浪潮推銷自己的拍攝意念,說服他出資,本質是一個電影工業的縮影。不過創作人成功獲得資金後,就可擁有完全的創作自由,不用受投資方的意向干預。 就這一點,在鮮浪潮誕生的作品可說別具個人色彩,能代表年青一代的聲音。他們有的關心受壓於香港政治社會環境的青少年、有的把目光投放在難解的家庭關係、有的書寫女性自主的戲劇、有的荒謬百厭。無論製作水平高低,我們都能猜想它們都是創作人的心血作品(理應不會出現為商業利益而拍的故事)。本來比賽制度容許作品 100% 的自由,現在卻接連遭受不透明的電檢制度,要求刪剪影片內容。有人決定一刀不剪,有人選擇「埋藏」不能過審的片段為應變辦法,他們都嘗試在狹縫中維護自己的心血,保護作為創作者的尊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