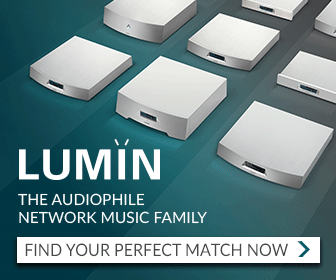《爆炸頭拿破崙》的電影手法,放回二千年初的語境,可算相當原創。導演通過電影的拍攝和剪接手法,充份展示拿破崙的格格不入(oddity)和非主流的價值觀。當荷里活電影以無縫剪接要觀眾投入,《爆炸頭》卻透過 off-beat 的方法令看者對電影的環境(加上美術和選景)和角色多了一點距離——偏偏這正是「正常」大眾和角色的距離。這種處理手法簡單,卻非常聰明,而且收效——拿破崙有一天放學回家,看到對面馬路的阿伯,正準備用散彈槍「人道毀滅」一頭老乳牛。但當他開槍時,散彈槍卻卡了彈。此時,載滿了學童的一架大巴士駛過,擋住了阿伯和乳牛,打亂了這場處決戲的節奏,卻令這場簡單不過的戲多了一重意義。電影並沒有再剪回阿伯和老頭的那一頭,依舊拍著那輛黃色大巴,然後「嘭」一聲,以牛的嗚呼和小童的慘叫作結。
Jerad Hess 把玩剪接和時機,去表達拿破崙充分斥著原始暴力與荒蠻的成長環境。然而作為主角的他也不是特例,這個環境衝擊鎮上的每一個小孩,包括大巴上的一群和看過太多而近乎麻木的拿破崙。觀眾如看慣荷里活電影,會被這種剪接處理殺個惜手不及,但不少的經典,如北野武的《花火》和 Aki Kaurismäki 的《列寧格勒牛仔》(Leningrad Cowboys)系列等,均採用 off-beat 的方法,帶出電影獨特的世界觀。無所適從的節奏,令觀眾不可能完全代入拿破崙,卻又對他的經歷有共鳴——難以融入群體,對自我懷疑等成長的迷惘。